嵊州[1]人在婴儿周岁时要大事庆祝,谓之“得周”或“闹周”。爷爷娘娘[2]外公外婆要给宝宝送上长命锁、手镯、项圈等首饰;婴儿当天要穿新衣,祭祖礼拜,以求余生平安顺遂。家长们则借着周岁酒,与亲朋好友们一聚,除此之外,还要去订做敲了红色喜印的糯米果。
我小时候,嵊州的糯米果多为乌豆沙馅,形状圆圆扁扁,似一轮雪白的圆月。包糯米果所用的乌豆沙馅制作费时费力,略过不述;糯米果的皮子则相对容易制作,只需将糯米充分浸泡后上屉蒸熟,再入石捣臼,加少许凉白开水反复摏打揉搓即成。刚包好的糯米果还留有余温,软糯香甜,分外好吃。糯米果的外皮铺了薄薄的一层糯米粉,一口咬下去,这糯米粉也就黏留在了嘴边,吃者好似长了一层淡淡白须,惹来观者一阵笑。糯米一冷就返生发硬,因此隔夜的糯米果不适宜直接吃,需用少许油细煎,待两面金黄即可食用。煎过的糯米果外皮略脆,内里却还是糯软香甜,而且传统乌豆沙里混有糖渍金橘碎,起到平衡甜腻之效,别有一番食趣。
除了糯米果,得周的人家还要给亲朋好友送红鸡籽——嵊州人说的鸡籽便是鸡蛋。小时候我最喜欢收到红鸡蛋,虽然只是普通的煠[3]蛋,但因蛋壳染了一层红而显得分外喜庆可爱。但每家的染色水平不同,有些红鸡蛋甫一上手,已将我的手指染得殷红。说来奇怪,这染料在鸡蛋壳上的附着力一般,到我手上倒用洗洁精洗上半天都未必消除得掉。
送糯米果和红鸡蛋的数量根据远近亲疏决定,不同亲朋赠送的数量差异巨大。至亲密友少说也要五十个糯米果打底,有些人家还会送上整数一百,可谓出手阔绰;关系远的亲朋则十个二十个糯米果配上几枚红鸡蛋表示一下即可。不过现如今,大家日常吃食丰富,糯米果送得就少了,据说每家十个二十个已成定例,很少有人一送就一百个起跳的了。
知道自己的抓周选择后,我对写作一事更有了种天注定的使命感。其实,我的写作兴趣非常宽泛,饮食写作之外,文学艺术历史经济等各个主题都有涉猎。但对饮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或许是流淌在我们家族血液里的,这本《小城回味志》可视为我对自己味觉审美体系的溯源之旅。
我太祖父在嵊县南门外大街开油米酱行,商号为“同发茂”,爷爷子承父业,据说一度将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我二伯在民国时,跟着爷爷在米行工作,后加入嵊县粮管局,对粮米油盐之道了然于心。我父亲虽然年轻时被分配到嵊县皮革厂工作,但在经历上山下乡和文革动荡后,他回归副食行业,在江滨路摆摊卖起了自制的糖果。他五十岁生我,当时我们家已在市心街经营一家品类齐全的副食品铺子。自有记忆起,我的生活中便充满了美味的零食、小吃和菜肴。外公外婆做了一辈子农民,种的也无外乎稻米小麦竹笋茶叶等食用作物,似乎我们整个家族都多多少少与饮食有些关系。正如我在《香港谈食录》序言中提及的,父母和姐姐都爱吃,而我母亲又擅割烹之道。种种因素迭加起来,令我这个成长于社会餐饮不甚发达的九十年代浙东小城的青年,对食物有了天生的兴趣和敏感度。
孝子坊
嵊州虽然只是个小县城,但它在饮食上有许多值得记录之处。嵊州人见面也爱以“侬饭有吃过咚哉”[5]为开篇,饮食渗透进了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我成长于斯的九十年代,此地的一切都欣欣向荣,人们的生活质量肉眼可见地提高着。同质化的快捷现代生活方式还没有侵染这个浙东小城,当时的嵊州人还保持着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和节庆习俗,我的童年便浸润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对节气风土的感知,对四季时令的执着,对传统生活美学的痴迷,都是我童年饮食经历留下的烙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嵊州市区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令许多美好的饮食文化和习俗异质化,生活美学随着生活便捷度的提高而显著枯萎。尤其在我离开家乡赴京读书后,高速的发展令全国一个个特色鲜明的小城镇逐步同质化,地方文化和方言逐渐丢失。作为一个历史的经历者,唯一能做的是尽己所能地记录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早在2012年,我就开始利用闲暇时间撰写嵊州饮食文化相关的回忆散文,后来将这些文章定名为《小城回味录》陆续在微信公众号“走走吃吃”上发布;最近几年,我也在《大公报》的专栏里发表过一些讨论嵊州饮食的文章,此乃本书之滥觞。
嵊州颇有特色的豆腐小笼包,时常惹我想念
2022年初,久无铁路的嵊州终于通了高铁,以前只能驱车或坐巴士前往的小城,如今有高铁可通,想必将有更多游客前往这千年古城探索。游客虽然增多,但随着本地老龄化的加重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近几年嵊州的人口总数一直处于下行趋势中。许多年轻人不仅对家乡文化知之甚少,连能说好嵊州方言者亦日渐稀少,嵊州文化的传承出现非常严重的断代问题。
考虑种种因素后,我觉得现在正是出版一本讨论嵊州饮食文化和习俗的散文集的好时候。香港三联书店的同仁们听闻我这一想法都表示支持。考虑到嵊州虽在内地有小吃名城的美誉,但在香港则知之者甚少,我担心这样一本关于嵊州的散文集是否会有销量。但三联书店的朋友们让我不要担心,他们相信出版这本书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在他们的支持下,我悬着的心终于定了下来。
去年完成《日本寻味记》卷一后,本想着有近一年时间可写作《小城回味志》。未曾想通关后事务繁忙,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旅行计划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临近交稿期限,才赶紧把心中打了千百次的腹稿写下,反复批阅增删数次,终于敢把稿子交给我的编辑宁础锋先生了。感谢宁编从不催稿,只做提醒,这让我感到我俩有十足的互信。感谢香港三联书店的李毓琪小姐、于克凌总编和叶佩珠总经理对本书和我本人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关心。感谢嵊州市商业发展集团的领导与同仁们在我回乡采风时给予我热情协助,也感谢帮我拍摄了部分配图的小学校友沈天虹同学。
感谢陈晓卿导演和李舒女士为本书撰写序言,感谢方晓岚老师和陈立老师为本书撰写推荐语,几位前辈的作品也是我寻味写作之旅上的重要灵感来源。
最后,我要感谢先君、母亲、姐姐和所有家乡的亲朋们。无论你们身在何方,你们的关爱始终是我在人生汪洋中勇敢前行的力量。没有你们,我就不会拥有如此美味的童年。本书写作期间,是我这些年与母亲和小娘舅交流最频繁的一段辰光。在我打破沙锅问到底式的追问下,他们与我一同回忆了许多陈年旧事。希望他们想起的都是快乐往事,至于那些遗憾与难过,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如今被拆到只剩下一小段的市心街是我成长的地方
《大公报》副刊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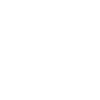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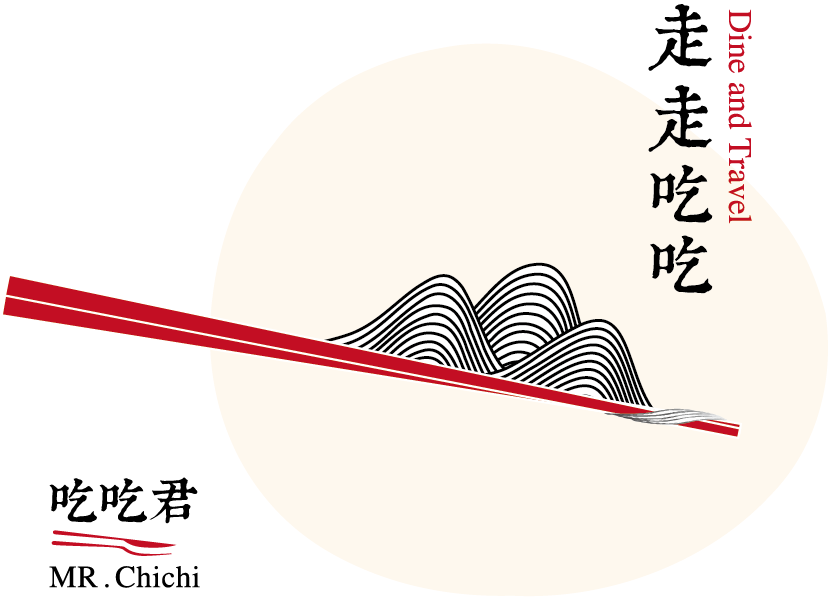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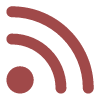 文章订阅
文章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