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兄弟姐妹六人,我的同辈表亲也人数众多,我与外婆并不算亲近。不知道是不习惯山里的气候还是小虫叮咬所致,从小一去外婆家住几天,身上便会发红点子,因此我很少在外婆家过夜。关于外婆的记忆都是逢年过节的那一次次短暂的看望组成的。这些记忆原本并不醒目,沉积在心底好似不存在一般。但二零一二年五月外婆去世了,从那一刻起,这些记忆却时常莫名地翻涌上心头。
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站在老灶边的外婆,她低垂的眼睛慈祥地望着我。皱纹满布的手握着锅铲,奋力翻炒着大铁锅中的菜,锅铲和铁锅摩擦发出一阵阵清脆的炒菜声……
自我有印象起,老灶就矗立在外婆家的灶间里。宽阔的灶头侧壁上有两个垂直凹槽,一个小些,放着些火柴和生火用的废纸;一个大些,供奉着灶神。一个大铁锅镶嵌在灶头中,旁边则是小小的煮水锅。高高的烟囱直通到屋顶,烟囱边挂着一个竹编饭篮,幽幽地悬在那儿,不顾世界的喧嚣。而这宅子也经历了数十年几代人的消磨,显得沧桑古老,甚至有些破旧了。
外婆家的味道总是混合着草灰的焦气、山花的清香,以及一阵阵难忘的炊烟气息。小时候我最喜欢坐在灶头后面为外婆生火,将散发着清香的松木屑放进灶门里,“呲”地划燃一根火柴将木屑点燃,趁着火正旺的时候放进木柴,然后用一柄蒲扇扇啊扇——有时候甚至要用毛竹管吹起生火——外婆则在灶前炒着菜。年幼贪玩的我喜欢不停地往灶门里加木柴,将火烧得又红又高,外婆则会嗔怪说“再烧就要把锅底烧穿了!”我则只管咯咯地笑着。灶堂里木柴慢慢烧成了黑色的炭,炭烧成了灰,落在了灶底,时间一长,灰色的炭灰好似柔软的棉被积了厚厚一层。刚落下的炭灰很烫,外婆便会在其中埋些番薯和土豆,做完一顿饭,这些小东西也正好被焐熟了。
老灶头是如此充满了魔力,即使是隔夜米饭,放在大铁锅里一回锅也变得饭香扑鼻,脆脆的一层锅巴更是让人爱不释手,咬得腮帮子疼都不肯停口。城里的电饭煲做饭省时省力,但却只是如此中规中矩得把饭煮熟了而已,灶头里煮熟的米饭有一种电饭煲米饭永远无法比拟的锅气。只要闻到那样的饭香,我就会想起外婆家的溪流山丘,就会想起每次我们回山里时,早已在村口眺望等待的外婆。
外婆最拿手的菜是大蒜叶炒萝卜和笋干菜蒸肉,这是再家常不过的菜了,但外婆却能把它们做得非常好吃。萝卜是外婆自己种的,去了皮,切成薄片。烧红铁锅后,放点香气扑鼻的菜籽油,把萝卜和着大蒜叶炒啊炒,一点点酱油调味,什么都不需要再放,一碗开胃的炒萝卜便做好了。母亲见我吃得那么欢,回家也如法炮制了几回,但全失败了。菜市场买回来的萝卜没有外婆亲自种的萝卜的口感,淡淡的甜味也不见了,个头虽大,但却寡然无味;家里的小锅更是炒不出大铁锅的锅气。
笋干菜也是外婆自己晒制窖藏的,猪是自家养的。正月里去外婆家一定会有这道需要火候和耐心的菜,每天外婆都会把这菜上锅蒸制两个小时,等到蒸了四五天时,猪肉已变得入口即化,肥油浸润到笋干菜之中,让原本有些干涩的笋干菜变得美味糯软,这时候吃这道菜是最享受的。外婆的笋干菜用雪里蕻和春笋晒制而成,首先将雪里蕻切成碎末,春笋切成细丝,然后用大锅炖煮,当汤水煮出菜汁,香气四溢时便蒸锅倒出放凉。待菜冷却后铺在竹篾筛子上,放在阳光下曝晒数日,等笋干和雪里蕻末都晒得精干即可。然后外婆会将晒好的笋干菜塞入大坛子中窖藏保存。冬日的午后,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外婆会用大铁锅烙出一张张薄软的麦饼,里面裹上蒸透的笋干菜和五花肉,拿来给我们当点心。吃完后,我们的嘴都是油露露的,那种感觉现在想来也会让我饥肠辘辘。
与家乡千里之隔的我
常常只能通过复刻家乡的味道来宽慰乡愁
小时候我觉得外婆如同这灶火般永远不会熄灭,每天挑水做饭,劈柴喂猪,还要照管那几亩茶田。每当逢年过节我们回去看望她,她反倒还要照顾我们这群调皮的孩童。外婆那小巧佝偻的身躯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家族。随着时光流逝,外婆的身体也如同这老灶头一般慢慢消耗了,前几年放假回去我才发现,短短几年间外婆竟已如此苍老。以前矫健的步伐变得蹒跚了,佝偻的身躯更是越发低垂,满头的灰发已成银白,那一年我给外婆拍了好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外婆和老灶的合影。一束阳光从屋顶的天窗射进来,使得外婆和老灶头都显得无比圣洁无比宁静。
外婆的年纪越来越大,慢慢的老灶头用得也越来越少了,毕竟提起那大锅盖也需要使出些力气。子女们早就给外婆买了煤气灶和电饭煲,可我每次回外婆家总还是念念不忘那灶头。去年正月里回外婆家,发现那灶头早已被烟熏黑,表皮也有些剥落了。很久前供上的灶神菩萨,原本光鲜的色彩早已暗淡成了一个灰黄的土坯子。厚厚的炭灰还堆积在灶坑里,只是已不再松软,也没有了火炭的气味,摸上去更是冰冷瘆人。一切都显得冷冷的,暗淡无光。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尝到那大铁锅饭的味道了,那种粗犷,乡土,甚而有些原始的味道早已被现代厨具的简便无趣所替代。而那一个个曾经忙碌在灶边的人们也逐渐离我们远去。
二零一一年秋天,外婆中了风,之后便卧病在床。最后一次见外婆是在二零一二年的正月里,那时候外婆躺在老宅的床上,我站在床边叫了几声“外婆”,她张大着嘴却没有声音。母亲对她说:“妈,还认得出这是谁吗?”外婆吃力地点点头,终于挤出一丝如喘息般的声响,勉强能听出她说的是“放假了啊?”我点点头,摸了摸外婆满是皱纹的脸庞,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待了没一会,想到时间已晚,还要赶回城里的家中,便走出老宅,穿过小巷,头也不曾回地上车走了。谁能想到这竟是永别?
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起老灶边的外婆。外婆微笑的脸庞,铁锅里蒸腾的热气,还有咯吱咯吱摇晃着的饭篮子……多么遥远的画面,显得那么不真实。我的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便去世了,因而我概念里的“老家”便是外公外婆的家,正月里母亲的一整个家族都会聚在那叫做岭根的山村里,老宅客堂中一个梨花木大圆桌,一大桌亲朋,一大桌菜,一片谈话声,一屋子笑声,这子孙满堂的团圆景象是传统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心愿。我虽然是八零后,但心中依然珍惜这份大家族的血缘之情。现在,外婆去世了,外公也住进了养老院,山村中的老宅想必早已灰尘满布,那种正月里的大团圆也不会再有,即使舅舅姨妈各家再聚在一起,也难以找回那种大灶老宅的温情,毕竟一个失去母亲的家庭永远都是残缺的。长大成人离开家乡之后,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我们如果失去了,那就是一辈子的擦肩而过了。
P.S.如今外公也去世了。老宅彻底空荡荡了。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满山的青梅依旧如雪绽放,山腰的薄雾也依旧飘荡,但老宅深锁,灶头经久不用,垮塌了一半,一幅破败样貌。曾经的欢乐时光真的已经彻底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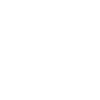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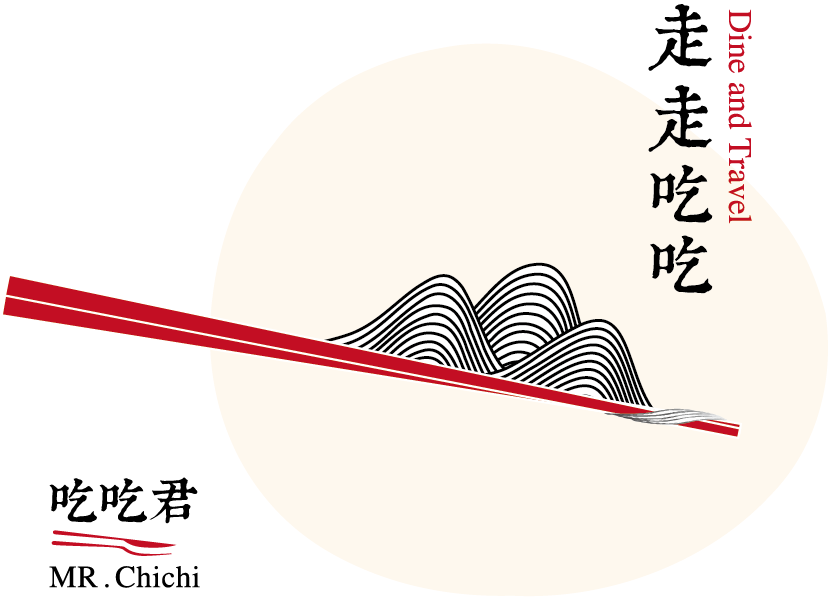
 文章订阅
文章订阅


